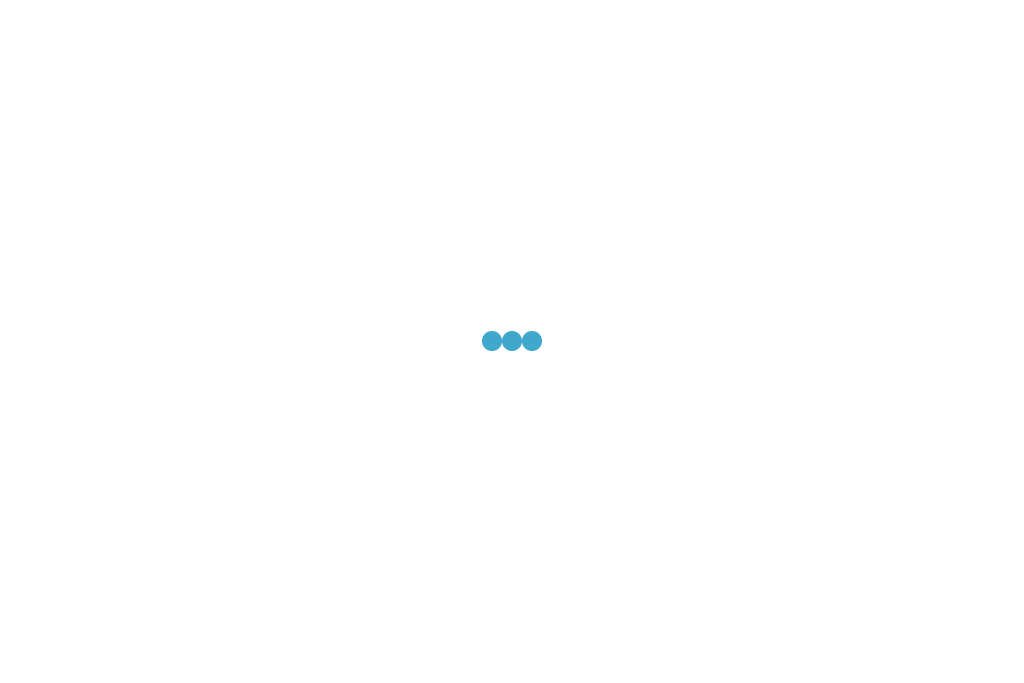作者简介

周斌
1968年生于重庆黔江。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东亚汉籍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东亚汉字圈国家汉文古籍整理与汉文史籍研究工作。
摘要:高丽王朝金富轼《三国史记》曾三次引用《新罗国记》,但皆误题作者为“唐令狐澄”,而令狐澄并没有撰写过《新罗国记》,也没有条件撰写。考其致误原因,乃是金富轼误读宋人所编《绀珠集》所致。《新罗国记》是中国的第一部新罗使行录,在中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真正作者是顾愔。《新罗国记》散亡于南宋建立之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之间。考各书所引,可辑得佚文四则。顾愔生卒年不详,各书皆不载其家世与籍贯。经考证,知与大诗人顾况为从兄弟关系,是苏州海盐县横山(今属浙江)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曾作为副使出使新罗,其从弟顾况为作《送从兄使新罗》一诗。顾愔所任本官不可考(疑为“从事”一职),所知者是出使期间曾兼侍御史(一说“监察御史”)一职。
关键词:顾愔 《新罗国记》 金富轼 《三国史记》 令狐澄 《贞陵遗事》 顾况
使节出使所撰记录其见闻的书籍,常被称为使行录。最早的使行录是汉代张骞的《出关志》,但此书《汉书·艺文志》不载,疑后人伪托。东晋南北朝,交聘朝觐记录渐多,如燕聘东晋的盖泓《朱崖传》,刘师知《聘游记》,江德藻《聘北道里记》,佚名《魏聘使行记》等。使行录至两宋而渐多(出使辽、金、元、高丽),至明清而极盛(出使朝鲜、琉球、安南等)。
唐代出使新罗的使行录有两种:《新罗国记》与《新罗纪行》。其中,唐代宗大历三年(768),顾愔担任副使出使新罗所撰《新罗国记》是最早的一部,所以,顾愔《新罗国记》在中外交流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有关唐代诸书皆无顾愔传记,致使后人连其家世与籍贯都不清楚,学术界也只是怀疑他与顾况是同一家族,但并无切实的论证。至于顾愔出使新罗,则未见有任何论著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顾愔出使新罗概况、顾愔家世与籍贯、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引用《新罗国记》误题作者为令狐澄等问题试作探讨。
本文在材料使用、研究角度等方面,试图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诗文与史籍互证;二是中国典籍与朝鲜半岛典籍互证;三是小中见大,即不但要考证此次出使的基本史实,更要归纳总结出唐代后期派遣出使人员的规定或惯例。
一
顾愔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出使新罗之概况,两《唐书》、《全唐文》、《三国史记》等书皆有记载。《旧唐书·新罗传》载:“大历二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乾运为王,仍遣其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命。三年(768),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以乾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仍册乾运母为太妃。”按,据高丽王朝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宪英即新罗景德王,乾运即新罗惠恭王。《新唐书·新罗传》载:“大历初,宪英死,子乾运立,甫丱,遣金隐居入朝待命,诏仓部郎中归崇敬往吊,监察御史陆珽、顾愔为副册授之。”《三国史记·新罗惠恭王本纪》载:“四年(768)春,彗星出东北。唐代宗遣仓部郎中归崇敬兼御史中丞持节赍册书,册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兼册王母金氏为大(太)妃。”
《旧唐书》及《三国史记》皆载此次出使为大历三年,《全唐文》卷49所载《册新罗王太妃文》亦记为大历三年,唯《新唐书》作“大历初”。据此可以断定,此次出使的年代是大历三年(768)。而拜根兴《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定为大历二年,当是误读《旧唐书》,以宪英卒年为出使年所致。
此次出使的使命,综合上引各书,主要有两项:一是吊祭新罗前王景德王宪英,二是册立嗣王惠恭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兼册嗣王之母金氏为太妃。耿湋《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诗“立君成典册,行吊奉丝纶”,也可间接证明此次出使的使命。
自唐玄宗时期始,出使新罗使臣的选择标准是:正使必善经学,副使必善弈棋。《三国史记·新罗孝成王本纪》载:新罗孝成王二年(738)春二月,“唐玄宗闻圣德王薨,悼惜久之,遣左赞善大夫邢璹以鸿胪少卿往吊祭,赠太子太保,且册嗣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璹将发,帝制诗序,太子已下百寮咸赋诗以送。帝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以国人善棋,诏率府兵曹参军杨季膺为副,国高奕皆出其下。”《旧唐书》亦载:“璹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璹等金宝及药物等。”这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的出使新罗,正使邢璹善经学,副使杨季膺善弈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出使新罗,元季方为正使,元氏虽为兵部郎中,但据《旧唐书》本传的记载,也曾“举明经”,可见也是善经学之人。马宇为副使,据李翱《秘书少监史馆修撰马墓志》记载:“公博览多艺,弈棋居第三品。”元季方、马宇恰好也符合上述出使新罗的正副使分别应当擅长经学和弈棋的条件。而此次出使人员,据前引《新唐书》记载,正使为归崇敬,副使为陆珽、顾愔,其选择是否也是擅长经学和弈棋的标准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有关诗文却透露了一些信息。独孤及《毗陵集》有《送归中丞使新罗吊祭册立序》一文:“天子以公身衣儒服、力儒行,行之修可移于官,学之精可专对四方,是故公任执法之位,且使操节以济大海,颁我王度于大荒之外。……将弘宣王风,诞敷徽言,使鸡林塞外一变可至齐鲁。”按,鸡林谓新罗。另,耿湋《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诗曰:“远国通王化,儒林得使臣。”由此可见,正使归崇敬也是因为善于经学的缘故而被选。两位副使的情况,因无典籍记载,是否有人善弈棋,已不可考。
据前引《新唐书·新罗传》,此次出使,两个副使是“监察御史陆珽、顾愔”。但是,钱起《钱仲文集》卷5《送陆侍御使新罗》一诗,则说陆珽的官职是侍御,即“侍御史”简称。从《新唐书》“监察御史陆珽、顾愔”的表述来看,陆珽与顾愔的官职应相同。既然钱起说陆珽的官职是侍御史,那么顾愔的官职也应当是侍御史。此外,《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玉海》卷一五三皆记,“大历中,归崇敬使新罗,愔为从事”,则出使新罗时,顾愔的官职是“从事”。据上,两个副使的职官在史书和文集中的记载出现了差异:一为监察御史,一为侍御史,一为从事。不过,钱起《送陆侍御使新罗》一诗所说侍御史乃当时人亲见当时事,可靠度应高于《新唐书》、《玉海》所载监察御史或从事,所以两个副使陆珽、顾愔是侍御史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陆珽、顾愔的职官,无论是监察御史,还是侍御史,从唐朝后期历次新罗副使的职官规律来看,都应当不是本官,而是兼官。如韩愈《顺宗实录》所载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副使马于(“马于”为“马宇”之误)是主客员外郎兼殿中监(“殿中监”当为“殿中侍御史”之误),又如太和五年(831)副使崔锷是太子赞善大夫兼侍御史,再如咸通六年(865)副使裴光是光禄主簿兼监察御史。以上例证足以说明:诸副使各有不同的本官,而其兼官则或为侍御史,从六品下,属台院,或为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属监院,亦称察院,或为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属殿院。据此,副使陆珽、顾愔作监察御史和侍御史都是可能的。但是,无论是监察御史,还是侍御史,从上述例证来看,都应当是指兼官,而非本官。
从唐后期历次新罗正使的职官来看,贞元十六年(800)正使韦丹是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正使元季方是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元和七年(812)正使崔廷是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咸通六年(865)正使胡归厚是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以上例证足以说明,唐朝出使新罗的正使例得兼或摄御史中丞。所以,此次出使的正使归崇敬亦兼御史中丞。
唐代台院、监院与殿院三者并列,而使臣出使新罗,正使例兼(或摄)御史中丞,副使则或兼殿中侍御史,或兼侍御史,或兼监察御史,其目的是在使行往来过程中,赋予正副使以执法权,独孤及在《送归中丞使新罗吊祭册立序》一文中所言归崇敬“任执法之位”,应当即是此义。当然,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此类宪职在当时仅是一种礼仪,而非实有职掌。
二
据前引《三国史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之出使新罗,“帝制诗序,太子已下百寮咸赋诗以送。”顾愔大历三年(768)这次出使是否仍有天子制诗序,太子以下百寮赋诗以送呢?史无明文。但前引独孤及《送归中丞使新罗吊祭册立序》言:“凡以诗贶别,姑美遣使臣之盛云尔。”此处“姑美遣使臣之盛”之主体不可能是平常人,只能是天子,说明这次也不例外,仍是天子制诗序,百寮赋诗以送。据各总集、别集所载,可以考知的送行诗,送正使归崇敬的有如下一些:皇甫冉《送归中丞使新罗》,皇甫曾《送归中丞使新罗》,李益《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耿湋《送归中丞使新罗》,李端《送归中丞使新罗》,吉中孚《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送副使陆珽的有钱起《送陆侍御使新罗》;送副使顾愔的是其从弟顾况《送从兄使新罗》。
当然,顾况《送从兄使新罗》并未说明此“从兄”就是顾愔,王启兴等《顾况诗注》曰:“从兄,疑指顾愔。”笔者断定此诗中的“从兄”就是顾愔,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遍查中国及朝鲜半岛有关唐代出使新罗的文献,顾况在世的八世纪初到九世纪初,唐朝出使新罗使者中,只有一位姓顾,那就是顾愔;第二,顾愔此次出使在大历三年(768),正是顾况四十岁左右。顾况写诗为顾愔送行之年,如在顾况幼童时期或其卒后,于年代肯定不符;而恰恰在顾况四十岁左右,于年代则不相冲突。所以,顾况《送从兄使新罗》一诗中的“从兄”,可以肯定为顾愔。顾愔其人,因无任何传记,如非顾况此诗,则后人将无从知其家世与籍贯。
既然顾愔与顾况是从兄弟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们应当籍贯相同。傅璇宗先生说:“顾况的籍贯,记载也有歧异,计有三说:一,苏州人;二,吴兴人;三,海盐人。”苏州说的主要依据是《旧唐书》卷130顾况本传及《唐才子传》卷8,傅先生对吴兴说作了有理有据的否定。而对海盐说,他认为:“见于《全唐诗》卷二六四的顾况小传,未知所据。”其实,海盐说是有较多依据的。考查海盐说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徐硕《至元嘉禾志》卷13:“唐顾况,吴郡海盐人,居县西南三十里之横山,以诗名。尝有诗云:‘家住双峰兰若边,数声秋磬发孤烟。山连极浦鸟飞尽,月上青林人未眠。’”按,《华阳集》卷中此诗诗题为《横山故居》。《至元嘉禾志》虽成书于元代,离唐代已较远,但通过一些唐朝诗句的佐证,其所载顾况为海盐人,应当说是可靠的。《至元嘉禾志》卷14载:“顾况宅在海盐县西南五十七里横山禅寂寺,寺侧祠况为伽蓝神。况尝有诗云‘家住双峰兰若边’是也。”此处所谓双峰,指海盐境内的大横山、小横山。很明显,《至元嘉禾志》是引用顾况的诗来证明顾况为海盐人。此外,唐刘长卿任海盐县令时,有《过横山顾山人草堂》诗,也可以作为顾况是海盐横山人的证据。自元朝《至元嘉禾志》提出海盐说之后,成书于明前期的《大明一统志》,以及明后期万历年间重辑的顾况《华阳集》卷首所载姚士麟撰《顾况传》,明末《天启海盐县图经》卷12《顾况传》,皆言顾况为海盐人,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及《全唐诗》顾况小传、《大清一统志》等,遂皆迳言顾况为海盐人。据《旧唐书·地理志》,隋吴郡,于唐武德四年(621)改为苏州,天宝元年(742)回改为吴郡,乾元元年(758)又复为苏州,而海盐为其属县。因此,说顾况是海盐县横山(今属浙江)人,不仅与《旧唐书》及《唐才子传》记载的苏州人不矛盾,而且比说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苏州或吴郡显得更为准确。而吴兴在今浙江湖州,与顾愔、顾况无关,确如傅先生所言,吴兴说实属错误。
《全唐诗》卷242有张继《送顾况泗上觐叔父》一诗:“吴乡岁贡足嘉宾,后进之中见此人。别业更临洙泗上,拟将书卷对残春。”这位顾况的叔父很有可能即是顾愔之父。顾况觐叔父于泗上,并不能说明其叔父长期居住于洙泗(今山东曲阜)或泗上,更不能断定其叔父的籍贯在洙泗或泗上,因为诗中明言是“别业”,没有其它资料显示顾况在洙泗有别业,故当是指其叔父之别业。顾况《虎丘西寺经藏碑》言其有叔父“讳七觉,字惟旧……八岁剃度……至德三年(758)示终本山”。而顾况于泗上所觐的“有别业”的叔父,按常理,应当不是这位少年即已出家的讳七觉的叔父,而是另外一位叔父。
《四库全书总目》言,《华阳集》的明朝万历重编三卷本,是顾况裔孙顾端所编。关于顾端其人,《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44引《海盐图经》曰:“顾端,海盐人,工诗画,精六书义,为上舍生。”据此可知,从唐到明,虽历时悠久,但顾氏子孙仍居于旧籍,说明这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家族;而且,明朝顾端的工诗画,显然与唐朝的顾况工诗画一脉相承,说明顾氏家族还是一个讲究家学承继的家族。有着如此传统的家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顾愔、顾况虽为从兄弟,但应有相同籍贯,而且长久居住地也应相同,那就是苏州(或吴郡)海盐县横山(今属浙江)。
三
高丽王朝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汉文纪传体正史,曾在卷四、卷五、卷九共三次引用《新罗国记》,但皆误题作者为“唐令狐澄”。而且,此书现存三个典型的朝鲜时代旧版本(即1512年刻正德本、显宗实录活字本、1710年翻刻显宗实录活字本)均误作“唐令狐澄”,其它旧版本亦复如是;“唐令狐澄”与“唐顾愔”二者,既非形近,亦非音近:可见,一定不是抄刻排印之误,而是作者金富轼之误。
《三国史记》在韩国、朝鲜、日本和中国均有校点本,从第一个带校勘记的此书日本整理本(坪井九马三、日下宽校点《三国史记》,日本吉川弘文馆1913年铅排本),到最新的中国校勘本(孙文范等校点《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杨军校点《三国史记》,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都沿误未改。学术界亦无论著纠正此误,致使此误自《三国史记》的成书之年(1145)一直沿袭到现在,而顾愔的创作之功也就长期被令狐澄取而代之。鉴于《三国史记》一书在东亚有着强大的影响,必须对此讹误加以考论并纠正。
为便下文考论,兹先据显宗实录活字本《三国史记》将所引三条《新罗国记》抄录如下:
《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真兴王三十七年:“唐令狐澄《新罗国记》曰: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笔者按,“尊事”,《说郛》所引作“争事”。
《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真德王八年春三月:“唐令狐澄《新罗记》曰:其国王族谓之第一骨,余贵族第二骨。”
《三国史记》卷第九新罗景德王十四年春:“望德寺塔动。”小字注文:“唐令狐澄《新罗国记》曰:其国为唐立此寺,故以为名。两塔相对,高十三层。忽震动开合,如欲顷倒者数日。其年禄山乱,疑其应也。”笔者按,“数日”不合常理,《绀珠集》所引作“四”,疑各有讹脱,当据《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所引作“数四”,如《后汉书》卷六五“帝甚重之,以纯兼虎贲中朗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四”之例。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新罗国记》的作者是顾愔。如《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顾愔《新罗国记》一卷,大历中,归崇敬使新罗,愔为从事。”《通志》卷六六《艺文略第四》:“《新罗国记》一卷,顾愔撰。”《玉海》卷一五三:“顾愔《新罗国记》一卷,大历中,归崇敬使新罗,愔为从事。”《宋史》卷二○四《艺文三》:“顾愔《新罗国记》一卷。”据上引宋元诸书所载,可以肯定:《新罗国记》的著作权应当属于顾愔。
综上,顾愔撰有《新罗国记》,不仅有上述史书记载作为依据,而且也符合其生平经历——出使过新罗,具备撰写《新罗国记》一书的条件。
相反,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令狐澄并未撰写过《新罗国记》,宋元明三朝诸书所记,令狐澄的著作只有《贞陵遗事》一种。如《新唐书》卷五八:“令狐澄《贞陵遗事》二卷,绹子也,乾符(874-879)中书舍人。柳玭《续贞陵遗事》一卷。”《通志》卷六十五载:“《贞陵遗事》二卷,唐令狐澄撰。《续贞陵遗事》一卷,唐柳玭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贞陵遗事》二卷,《续》一卷,唐中书舍人令狐澄撰,吏部侍郎柳玭续之,澄所记十七事,玭所续十四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六:“《贞陵遗事》二卷,《续》一卷。陈氏曰:唐中书舍人令狐澄撰,吏部侍郎柳玭续之,澄所记十七事,玭所续十四事。”元脱脱《宋史》卷二三○《艺文二》:“柳玭《续贞陵遗事》一卷,令狐澄《贞陵遗事》一卷。”按,《宋史》所记“《贞陵遗事》一卷”,“一卷”恐是“二卷”之误。令狐澄《贞陵遗事》直到明朝仍然存世,如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二载:“令狐澄《贞陵遗事》一部一册。”《贞陵遗事》书名中的“贞陵”是唐宣宗陵墓名,而唐宣宗年号为“大中”。到了宋朝,因避宋仁宗讳,《贞陵遗事》遂改称为《大中遗事》、《正陵遗事》、《真陵遗事》、《真陵十七事》、《宣宗十七事》等。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四上又作《天中遗事》者,当是“大”与“天”形近而讹。
而且,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令狐澄也没有条件撰写《新罗国记》。令狐澄,据上引《新唐书》卷五八的记载,是令狐绹之子,乾符年间曾任中书舍人;又《新唐书》卷七五下亦载其为令狐绹之次子。而《旧唐书》却载其为令狐缄之子,卷一七二《令狐楚传》曰:令狐楚弟令狐定,“定子缄,缄子澄、湘。澄亦以进士登第,累辟使府”。咸通八年(867),令狐澄曾为其堂叔令狐紞撰写过《唐故朝散大夫比部郎中兼侍御史知度支陕州院事令狐府君墓志铭并序》,题“堂侄浙江西道观察判官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柱国赐绯鱼袋澄撰上”。《万姓统谱》卷一三六又载令狐澄曾当过东宫属官“詹事司直”。据上,令狐澄做过使府之官,咸通年间曾任浙江西道观察判官,还任过詹事司直,乾符年间任中书舍人。也就是说,令狐澄曾在唐中央和地方都做过官,但并无出使或游历新罗的经历,也就不具备撰写《新罗国记》一书的条件。
然则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引用《新罗国记》一书时,为何要将其作者名题为令狐澄呢?经考证,是金富轼误读宋人所编《绀珠集》所致。
《绀珠集》卷十引《大中遗事》,书名《大中遗事》作大字一行,其下有双行小字注(双行小字与大字在同一行),右为“令狐澄”,左为“《新罗国记》附,柳玭《续十四事》附”,其后为引文,现将引文抄录如下:
挼叶成钱:轩辕先生居罗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叶满手挼之,悉成钱。
气攻发直:先生又能散发箕踞,又用气攻其发,一条条如植。
对脉:唐宫中以诊脉为对脉。
天子须博览:裴恽进诗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比我?”宰执奏:“晋平吴,改元太康。”上曰:“天子须博览,不然,几错罪恽。”由是耽味经史,夜观书不休,宫中窃目上为老博士。
第一骨:《新罗国记》:其国王族谓之第一骨,余贵族为第二骨。
望德寺塔动:国为唐建此寺,故以为名,两塔相对,高十三层,忽震动开合,如欲倾倒者四,其年安禄山乱,疑其应也。
花郎:择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
老儒生:宣宗夜艾犹观书,烛灺委积,近侍呼之为老儒生。
播皇猷:上明于音律,常制曲曰《播皇猷》,皆方履高冠,连袂而舞,有曰葱西踏歌队者,大率其词言葱岭之士乐河湟,故曰归为唐民,又有执旛节者,如翔云飞鹤之变。
瓯水为酒:上作诸王时,常从猎坠马,困渴,求酒欲饮,以水,变为醪。
考《绀珠集》标题的大小字安排,应理解为《大中遗事》的作者是令狐澄,除引用此书外,还附带引用《新罗国记》、柳玭《续十四事》。《绀珠集》的编者没有将小字“《新罗国记》附”与小字“令狐澄”放在同一行,而是将其与“柳玭《续十四事》附”放在同一行,说明其编者很清楚,令狐澄不是《新罗国记》一书的作者,如同《续十四事》的作者也不是令狐澄一样。只是《绀珠集》的编者偶然失误,未将《新罗国记》一书的作者标注出来,从而可能让读者误认为《新罗国记》一书的作者也是令狐澄。
“第一骨”条特地标明出自“《新罗国记》”,说明“第一骨”之前的各条皆出自令狐澄《大中遗事》。但从上面引文来看,引用《新罗国记》止于何条,引用“柳玭续十四事附”起于何条,界限并不明显。宋人曾慥《类说》卷21也引用过上文,题为“《大中遗事》,柳玭《续事》附”,所引文字唯独少第一骨、望德寺塔动、花郎三条,其它文字略同。老儒生、播皇猷、瓯水为酒三条所记事件,发生于唐朝宣宗大中年间(847-858),在顾愔出使新罗的大历三年(768)之后近百年,顾愔不可能活得如此之久,而且,这三条记载也与新罗完全不相干,因此,不可能是顾愔《新罗国记》的记载。两相对比,可以断定,《绀珠集》引自《新罗国记》的是中间的第一骨、望德寺塔动、花郎三条,而老儒生、播皇猷、瓯水为酒三条出自柳玭《续十四事》(即《续大中遗事》或《续贞陵遗事》)。
《绀珠集》一书,旧题宋朱胜非(1082-1144)编,《四库全书总目》曾予怀疑,但不管其编者是谁,此书因有南宋绍兴丁巳(1137,绍兴七年)灌阳令王宗哲初刊序,称《绀珠集》“不知起自何代,建阳詹寺丞出镇临汀,命之校勘,将镂板以广其传”,说明此书早在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刊刻以前即已成书,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金富轼(1075-1151)《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即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因此,金富轼是有条件看到《绀珠集》一书的抄本的,甚至还有可能看到绍兴七年(1137)的刊本。只不过金富轼误读了《绀珠集》,以为《新罗国记》与《大中遗事》一样,也是令狐澄所作,从而在转引《新罗国记》一书时,直接在所撰《三国史记》中题为“唐令狐澄《新罗国记》”,致使顾愔的创作之功长期被令狐澄取而代之。
可能有人会认为,会不会是令狐澄《贞陵遗事》(即《大中遗事》)一书转引了《新罗国记》呢?答案是否定的,证据有三。
首先,上引《绀珠集》的标题可以说明,它主要是引用令狐澄的《贞陵遗事》(即《大中遗事》),附带引用《新罗国记》和柳玭续十四事(即《续贞陵遗事》)。如果所引《新罗国记》的内容是转引自《大中遗事》,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在标题小字注的第二行特地标注“《新罗国记》附”这五个字。
其次,《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景德王本纪》十四年载:“望德寺塔动。”据此,“望德寺塔动”发生的年代是新罗景德王十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而《贞陵遗事》一书,据其书名“贞陵”二字,当成书于唐宣宗死后,且应当记载唐宣宗(846-859在位)在世时发生的事情。所以,书名既然为《贞陵遗事》,它就不会记载发生于唐宣宗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事,更何况这件事还不是发生在唐朝,而是在新罗。
第三,令狐澄《贞陵遗事》全书所记仅有十七事(见上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罗宁先生已经将其全部辑佚出来,并无引用《新罗国记》的条目。
实际上,《绀珠集》不标注《新罗国记》作者顾愔之名的偶然失误,不仅误导了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也误导了几种中国书。如宋朝吴箕《常谈》:“《大中遗事》: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这是《新罗国记》“花郎”条的内容,吴箕《常谈》却直接将《新罗国记》视为《大中遗事》。又如两宋之际的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四上:“《新罗国记》:其国王族谓之第一骨,余贵族为第二骨。《天中遗事》。”按,“天中”为“大中”之误。元陶宗仪《说郛》卷四九引令狐澄《大中遗事》亦载“第一骨”及“花郎”两条。清人所编《御定骈字类编》卷二○二:“花郎,令狐澄《大中遗事》、《新罗国记》:其国王族谓之第一骨,余贵族谓之第二骨;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花郎,国人皆争事之。”很明显,以上三书皆视《大中遗事》转引《新罗国记》。当然,大多数中国古籍并未被《绀珠集》误导,要么标注为“顾愔《新罗国记》”,要么不书作者名而标注为“《新罗国记》”。
顾愔《新罗国记》一书的佚文,除前引《三国史记》及《绀珠集》所引相同的三条外,还可以从南宋初年吴聿《观林诗话》辑出一条:“唐人多作五粒松诗,有以五粒为鬛者。大历時,监察御史顾愔《新罗国记》云:‘松树大连抱,有五粒子,形如桃仁而稍小,皮硬,中有仁,取而食之,味如胡桃,浸酒疗风。’”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五一、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七六、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卷三上、清《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五九亦引此条,皆称引自顾愔《新罗国记》,而南宋初期《新罗国记》即已散亡(见下),故以上四书所引,恐皆是转引自《观林诗话》。
两宋之际的《绀珠集》及南宋初年的《观林诗话》皆引用过顾愔《新罗国记》,说明其时此书尚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崇文总目》卷四载:“《新罗国记》一卷,阙。”按,《崇文总目》虽编成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但是,《四库全书总目》考证云:“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言:乞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所阙之书,注‘阙’于其下,付诸州军照应搜访。”据此,则《崇文总目》卷四所载“《新罗国记》一卷,阙”,并非指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此书已阙,“阙”字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新添加的。到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王应麟《玉海》所载新罗事虽极多,但并未引用过《新罗国记》,仅是抄录前引《新唐书·艺文志》的内容,说明王应麟未见过《新罗国记》,《新罗国记》此时当已亡佚,此后的各种目录书亦不记载《新罗国记》。因此,顾愔《新罗国记》应当散亡于南宋建立之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之间。
综上,顾愔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曾作为副使出使新罗,其从弟顾况为作《送从兄使新罗》一诗。顾愔所任本官不可考,或为《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及《玉海》卷一五三所载“从事”一职,所知者是出使期间曾兼侍御史(一说“监察御史”)一职。顾愔撰有《新罗国记》一书,此书散亡于两宋之际,今可辑得佚文四条。顾愔与大诗人顾况为从兄弟关系,是苏州海盐县横山(今属浙江)人。金富轼《三国史记》引用《新罗国记》误题作者为“唐令狐澄”,其真正作者是顾愔。考其致误原因,乃是金富轼误读宋人所编《绀珠集》所致。
【注】文章原载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责编:李毅婷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头条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