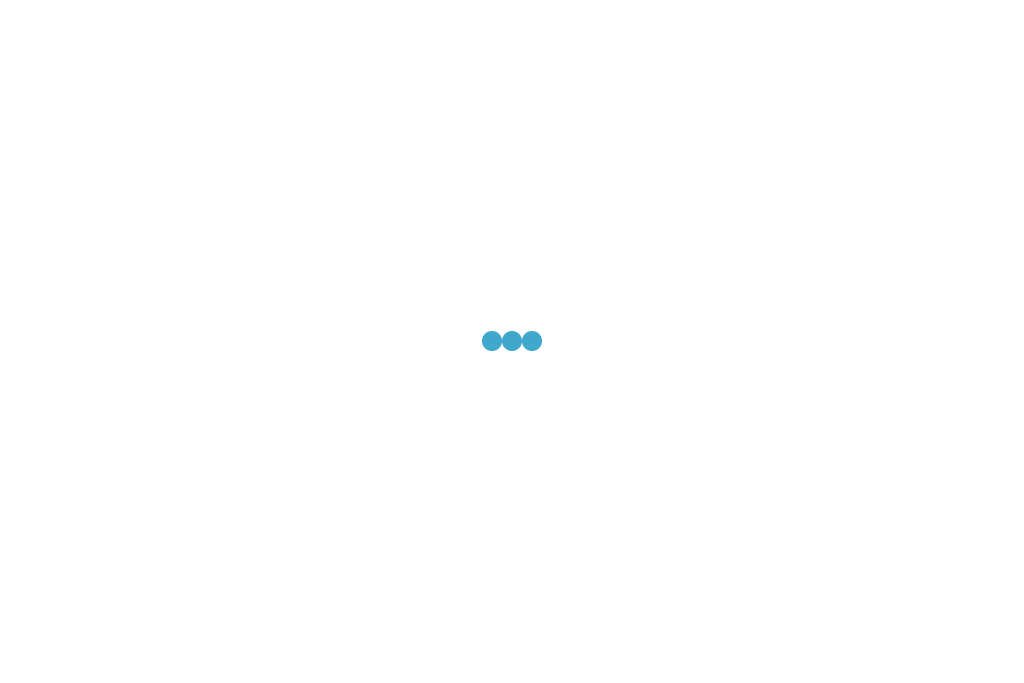【作者简介】丁存金,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
【摘要】方国瑜因心系西南边疆而回乡任教四十余载,一生勤勉治学,成为一代滇史拓荒的大家,在云南地方史、民族史、西南边疆史、云南地方文献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丰厚。方国瑜在梳理云南地方史期间,留心研究空白的元代部分,悉心收集整理史料并对元代西南史地详加考释,成为元代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
【关键词】方国瑜;元代;西南边疆
元史研究历来呈现重北轻南的现象,而西南部分在早期研究中可谓是空白的,方国瑜先生留心研究空白的元代部分,悉心收集史料完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史料丛刊》、《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并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民族史讲义》中对元代云南史地详加考释。先生一生辛勤耕耘、筚路蓝缕,诸多著作中叙述元代之部分及专述元代时期的多篇文章为元代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元代云南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元代现存文献资料较少,一直成为此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难点,而方国瑜先生不畏困难,对于各方史料搜访殆尽,比勘考辨,形成云南元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大全。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三中,方国瑜对各种史料文献爬梳分类,形成纪年及传记、政事、纂录史事、地理志、旅行记、诗文集六类,每一类目下虽篇目很少,但方先生对于每一能见之文献做出题解概说,明其源流,对于有讹误的则详加辨析考证。
《元史·本纪》是较为可靠的史料,记载云南史事一万一千余字,相对于《明史·本纪》的二千二百字、魏源删削的《元史新编》、柯劭忞错讹较多的《新元史》,《元史·本纪》资料的完整和可靠性不言而喻。方先生借张之洞《书目答问》之语认为毕沅之《续资治通鉴》“此书并非精审之作,不宜估价过高”。方先生说“言云南史事者,往往忽略边境,则由于史料少且不明确而被歧视。”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西南夷用兵”条是有开创性的见识之作。清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搜集史料丰富,可补正《元史》之不足。
《经世大典》是元代纂修的重要政书,《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纂录有《经世大典》中的征云南录、招捕总录、站赤篇、屯田篇、征建都录等内容,《元史·兵志·屯田》、《元史·选举志》、《元史·百官志》、《元史·食货志》、《元史·兵志》亦收录其中。《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黄元征缅录》一条,《云南史料丛刊》未收其文,方国瑜先生1938年撰有《元朝征缅录笺证》一文,对外国学者大力宣扬大缅族主义破坏缅甸国内民族团结的情况予以了回应。
对于地理志之类目,方先生引向达“《元史·地理志》记云南历代地理沿革,本末燦然,其所据必为所得大理图籍”语。认为“《元史·地理志》有较高之史料价值”。方先生考证《元史·地理志》所载南诏、大理事迹认为大理时期建制沿革可考,《云南图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元一统志》残本记有云南丽江府巨津、通安二州的建制沿革,有关唐代时期的记录不足为信,惟元初的记录实为有根据。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云南行省部分与《元史·地理志》参校互有补苴。元《天下城邑》乃是一部罗列各地路、府、州、县政区名号的书,就云南行省部分与《元史》记载不同之处,方先生认为对于他书没有之内容,《天下城邑》所记则可提供参证,柯劭忞之《新元史》虽有《元史·地理志》之外的政区地名,但出处可信度较低。李京所撰《云南志略》,在三序之外仅可见诸夷风俗,方先生认为陈文编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就是以其为主要依据,因此仅就记载内容而言,或可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观一二,《云南志略》也是考校南诏、大理纪年的有益之书。
对于旅行记之类目,郭松年《大理行记》是难得的史料,方先生据《中庆路儒学记》考校认为“松年至大理,应在至元二十五年之前,亦即在十七年至二十年之间,《大理行记》即此行所作。”并就《大理行记》所说云南地数百年间在经历蒙、郑、赵、杨、段五姓统治,但始终派使臣通与中国,仍可见故国遗风。因此方国瑜先生阐述了其“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理论观点:“故此数百年中,云南为中国整体之一部分,不能以统治者之分裂,而认为脱离中国也。”
方国瑜先生取《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一六章至一二八章完成《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刊于一九三九年《西南边疆》第四期。《马可波罗行纪》为考究元初云南史事重要史料之一,方先生对此的研究逐渐深入,最终与林超民教授共同形成《<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一书,对于《马可波罗行纪》中涉及的云南行省和缅国的政区、马可波罗在这一地区旅行的具体路线、元朝征缅、社会经济、宗教习俗等作了深入的探索考订,分类纂录,并就行记记录之多种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而且到过云南、缅国诸地,对国际上长期质疑此问题的人给予了有效回应。而其他有关的外国文献方先生特别提到波斯国拉施特的《史集》,其中特别指出关于云南的即契丹之第十省哈剌章及金齿,另有佛教典籍《指空行记》所载云南地名多可信。
对于诗文集之类目,《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收录元代之诗文集共一百多条,均是有关滇事的重要史料。碑刻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关元代云南史事的碑刻就流传有很多,“方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中收有元碑九十七目( 其中‘待访’三十七目) ,对各碑均作了题跋,详加考证。”有关金石文献之类目,方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不仅逐条分析,考证、辨伪,更有诸多碑文内容附录其中,对于今天已经失传的碑刻,是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
总而观之,方先生一生筚路蓝缕,勤于攻坚,终能为后世留下如此宝贵的元代云南史事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其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中说“史料学,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之一。做好这项基本工作,有助于历史研究做出成绩;而这项基本工作,是复杂繁重的,是要费力气的。”方先生甘坐冷板凳,对各种能见之史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诸多史料汇编于《云南史料丛刊》,可谓泽被士林,嘉惠后者。

二、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
1943年方先生整理旧稿,并多方请教其他学者,后修改而成《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中亦收录。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有弁言一则,绪论两则,傣那区域史料编年,元代傣那区域地理,傣泐区域纪事,元代傣泐区域地理和附录的傣族区域风土记等几部分的内容。
绪论中论述元代以前傣族的居住区域和见于记录傣族的名称两部分内容亦占据全书三分之一,对于研究傣族区域的社会历史和元代的东南亚关系史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小泰区域,即湄南河上游及以北地区,有益奴、兰那、速古台等大部落,益奴即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庸那迦。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庸那迦包有的车里、金城、景迈、速古台等几个小国纷纷呈现独立状态,各自成为真腊的属国。方先生认为小泰北部兰那国在公元1188年的瓦解,可能因车里境内出现了景龙国。景龙国的范围则包括有景龙、兰那、猛交、猛老和叭真等区域,即包有元明时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而对于傣族何时起进入车里区域,方先生认为有待考古证据的发掘。大泰区域主要是怒江以西地区,伊洛瓦底江上游东西地带主要有掸族和缅族,而在此以东的永昌郡区域则是金齿部落。
傣族在历史上有着多种不同的他称,按照樊绰的记载,唐代时南诏境内的永昌城就有金齿等十余个部落,其中金齿、银齿、黑齿、繍脚、繍面等均是因其习俗而称之,不是族属的专称。“金齿之名,缘于俗尚,自唐迄元称之。”方先生认为元代云南行省西南广大的区域,以金齿族为主要,但不限于金齿族,金齿之名是指错杂而居的各族组织部落。“金齿等处宣抚司,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明代时金齿区域的土司几乎都是傣族,所以可推测出元代时金齿族已经逐渐成为统治民族,这一区域已经是傣族势力区域。大理国政权统治茫人地区后,该区域的金齿族逐渐由散居进入到一个相对集中地状态,相比于其他部落,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永昌之南还有茫蛮,其习俗与金齿相同,也是傣族的一种他称。另外还有白夷(又作白衣)、僰夷者,亦是傣族。
方先生搜集了《云南志略》《元史》《经世大典》《腾越州志》《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牧庵集》《新元史》《蒙兀儿史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史集》《明史》《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百夷传》《滇考》《马可波罗行纪》《通制条格》等诸多文献以及元代云南碑刻等资料中的有关傣那、傣泐区域史事的条目进行了编年,并对两区域的地理进行了考释。
傣那地区是元朝征服云南后最先统治的一个重要区域,因此在该地区设置了诸多政区,方先生通过对元、明文献记载的梳理和研究,对傣那(金齿)地区政区设置的时间、地理位置作了考证。柔远、南甸、镇西、茫施、平缅、麓川、镇康、孟定、谋粘、木连十路及银沙罗甸在怒江两岸,为金齿部之东境。蒙光、云远、蒙怜、蒙莱、太公、木邦六路及缥甸、孟并、孟广、通西等在麓川平缅之西,为金齿部之西境。整个元代,金齿地区设置的政区计有21个。
傣泐地区与傣那区域相连接,包有车里、八百媳妇、老挝等广大区域。元朝统治傣泐地区始终都不如傣那地区稳定,因此政区设置的数量也并不多,主要有彻里路、木朵路、木来州、孟隆路、耿冻路、耿当州、孟弄州、孟爱甸、蒙兀路,刀连、刀盖、蒙样、蒙威、蒙凹、蒙列等甸。傣泐区域范围广大,内部不稳定,因此元朝的统治也未能深入,所设政区长官也多委当地的土官担任。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篇末附录《傣族区域风土记》,这是对傣族社会风俗史料的整理,增加了很多明、清地方志书中的材料,虽无概说考证,但对于形成一部完整的傣族史亦大有裨益。
与《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互鉴的还有《傣族简史草稿》一书,成书时间约在1958年后。方先生的傣族史研究是以元代为切入点,精于史料搜集和深入考证,充分体现了方先生深厚的治学功底和大家学术风范,不仅丰富了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更填补了云南地方史研究中元代部分的空白。段瑞认为“《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是方国瑜先生完成的唯一一部民族史料编年,它不但为我们研究傣族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如何搜集、整理、分析民族资料的科学典范。”

三、整体性视野下的元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元代是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云南行中书省建立后,中央逐渐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经营。方国瑜先生对元代史料知之甚多,虽未专注于作此时期的断代史研究,但是在其长期的云南地方史研究中,也形成了诸多元时期有关西南边疆史地问题的重要论断。
(一)上承南诏、大理国史研究,揭示元朝对云南实施统治的历史必然性
“一个政治单位,是以一个地区为中心联系广阔区域。”自西汉在西南设置郡县迄隋唐,云南滇池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已经发展水平很高,洱海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形成区域中心,“西洱河地区在初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已臻发达”。唐王朝在西洱河地区的设姚州都督府并支持南诏统一,南诏崛起后不断征服西南各地土长加强统治,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政权逐渐建立,形成“东至大唐,南至交趾,西至摩伽陀国,北至吐蕃”的广大疆域。
南诏的统治疆域内直接控制区域有十赕、七节度、二都督。南诏晚期,洱海地区逐渐由奴隶制进入封建时期,新兴阶级逐渐取得统治权,虽经历郑、赵、杨、段、高的权力更替,但是都继承了南诏时期的规模,“守其疆理,且更稳固,沿其区划,且更加密,则历史发展所必然。”五代两宋时期,“内地的经济文化传播到西南地区,较之以往更为发达,社会基础发展较快,到大理段氏后期已很繁荣。”大理国时期的疆域范围虽无明确记载,但是从元代记载和杨佐的记录可知其大概。大理国前期沿南诏旧制,除首府之外,设二都督、六节度为大府。大理国后期,政区设置上调整为八府、四郡、四镇。《元史·地理志》记有各政区的历史沿革,南诏、大理的因袭情况均有提及。元朝征服云南后二十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设置诸多的路、府、州、县,已经和内地各省差别不大,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基础决定的,而这样的社会基础得益于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对云南地区的经营和拓展。
方先生本着“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此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基础”的指导思想,长期致力于南诏大理史研究,认为大理国时期这一区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上承南诏,下启元代云南行省”的特点,揭示了元时云南入中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必然性。
元代以前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时分时离,所以方国瑜先生就南诏、大理时期的在西南地区加封号的边州性质情况作出论证,认为南诏、大理依然是中国历史的范围,强烈驳斥王朝统治以外的中国领域不在中国历史范围以内的看法。方先生特别强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尤其族别之间更为显著。方先生认为“把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是极端荒谬的。把落后地区的政权称为羁縻来区别于郡县,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史与王朝史应有所区别,王朝的疆域不等于中国的疆域,王朝的历史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云南地区历经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发展,政区不断出现调整并非偶然,是伴随其内部社会经济体制变化而演进,且该地区主流文化还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恰如郭松年《大理行记》中所说的有“故国遗风”。
方先生特别以云南各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例说明了云南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关系,云南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内,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外,若以王朝史观来决定云南之于中国之内外,“不惟云南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不能系统阐述,也破坏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政权的分立,并没有割裂了中国的整体,而且更加强烈地要求整体的发展,终于实现了统一。”元朝兵征云南纳入一统,是隋唐以来云南政权统治者谋求与内地王朝联系的新时代转折点。
(二)元明清三代西南地区疆域沿革和设治的总体考察
《元史·地理志》记载大理国疆域:“其地东至普安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元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稳定的统治,并继续向西南扩展,在蒲甘地设置了邦牙宣慰司,与登笼(得楞)国联系至海上,并收八百设宣慰司、服老告设总管府。方先生认为这是在段氏势力所及的基础上,元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并逐渐稳定下来。
云南行省建立后,赛典赤·瞻思丁奏请更定诸路名号,云南行省之下的路、府、州、县逐渐得到设置。《元史·地理志》记载云南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次数。”方先生又据《赛平章德政碑》、《世祖平云南碑》、魏源、柯劭忞的记载之不同,认为“自初设行省至元亡的一百余年中,地方行政区划,兴革不常,诸多记载都未为完备,只可知其大概。”
对于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地名考释,方先生以丰富的史料论证十分详细深入。在考释元初五城(鸭赤、哈剌章、察罕章、金齿、赤秃歌儿)时,明确了鄯善为中心的鸭赤和大理为中心的哈剌章、摩沙人为主的察罕章、金齿族(傣族)区域为五城之一、赤秃哥儿在滇东以东区域之鬼蛮,同时指出了夏光南、伯希和在相关问题论述中的一些错误。元初五城所辖之范围是云南行省建立的主要基础,在《<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中对五城的范围亦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元朝在云南行省设置了十三个宣慰司或宣抚司,方先生认为云南的宣慰司和宣抚司兼军政之务,虽委命流官,但也有土官,实与内地之宣慰司不同,只因除滇池四周和洱海地区外,其余地区尚处于地主经济前的阶段,因此宣慰司兼行都元帅之职,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
对于元代郡县地名,方先生结合明、清所记之名号及疆界进行了考释,分中庆、曲靖,大理、楚雄,乌蒙,丽江、北胜,永昌、顺宁、麓川,景东、元江、车里,临安、开化、广南,罗罗斯,罗甸、亦奚不薛和西南边疆十一个区域展开。在每一区域的考释过程中,方先生将元、明、清及近代之郡县名称列表作对照,有变动之处则附注于后,所引文献兼及地理类史书、省志和府、州、县志等,为元代以来云南政区的变化提供了可靠的索引。除政区地名外,方先生亦对城镇甸寨地名、山川名称等地理进行了考证,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元代云南的面貌,并使我们对明清时期的情况有所认知,正如其所说“中国西南边界汉时已具轮廓,惟此地区社会发展较为延缓,设治稀疏。南诏以来,历大理前期、后期、元代至明初而渐加密,此过程是在疆域之内社会基础逐渐发展,并非疆界之逐渐扩大。”

四、积极服务现实需要的奠基者和引路人
方国瑜先生治学严谨,是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也是引路人。先生是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出于爱国爱家的情怀,希望能通过学术研究服务于时局需要。
1935-1936年间方国瑜先生随李根源参加了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勘察工作,对西南边疆危机有着切身的体会,并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对云南边疆的了解并不充分,导致在边界纠纷处理中失地颇多,因此毅然决定投身到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中。
1936年刚到云南初期,方先生经常听袁嘉榖、周钟嶽等老前辈讲云南掌故并向他们请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发现老先生们多谈论的是明清以来的云南掌故,对于明清以前的,尤其是有关少数民族的谈及很少,而当时的云南少数民族史研究也还基本是空白,因此他最早开始整理元代的史料并辑录出来。
方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元史研究需要做拓展和深入,其曾有意编写一部《元代云南史》,专门有两年时间搜集整理元代云南部分的史料,1936年任教初期,方先生经常在图书馆读书,元代史料的收集想应是在此时期完成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内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内迁,来昆者不在少数,在时代背景的影响和需要下,开展边疆研究迎来新的契机。1938年,方国瑜与凌纯声、楚图南等人创办了《西南边疆》杂志,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阵地。1942年国立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方国瑜先生等人又广泛开展云南、西康、贵州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又及安南、缅甸、印度、马来半岛诸境的历史和社会调查研究。也就是从1938年以后,方国瑜先生的研究多为时局所牵引,南诏大理国史的研究也就是在此阶段伴随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和伯希和的相关错误论断而开展和不断深入的。
方先生的元史研究看似中断,实则愈加深入,先生将元代云南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运用到了元代之前后各时期的历史研究中,真正实现了以元代为基点贯通云南历史的目的。1938年冬,方国瑜先生开始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写成《疆域沿革》、《金石考》、《宗教考》等,修定《族姓考》,1944年发表《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1945年写成《云南沿革》,1963年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1961至1973年间又参与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最终形成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在方先生整个的研究历程中,他积极服务于时局需要,虽未完成《元代云南史》,但依然把元史研究的成果贯穿在一生的各阶段研究之中。方先生虽自言无心于断代史研究,大抵因为其愈加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学术探索》2019年第3期。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